近日,我院副院长李家莲副教授的文章《论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中情感与规范的断裂》于《道德与文明》刊发。
论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中情感与规范的断裂
〔摘要〕作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学派中的首位思想家,沙夫茨伯里把道德判断的本性理解为审美判断,主张基于以审美为本性的苦乐感为道德规范奠定情感基础。但事实上,以这种苦乐感为表现形式的审美情感无法为道德规范奠定有效的情感基础,确切地说,情感和规范在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中呈断裂状态,因此,他的情感主义哲学未能建立有效的规范理论。尽管如此,由沙夫茨伯里建立的这种道德哲学对17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具有的重要革新意义和对18世纪道德哲学具有的开创性价值和启蒙意义却不可被忽略。
〔关键词〕沙夫茨伯里 情感 规范 审美
从情感出发理解并构建道德规范理论是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面临的核心理论任务。该派道德哲学以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Anthony Ashley Cooper,3rd Earl of Shaftesbury,后文简称沙夫茨伯里)、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核心代表人物。不过,在基于情感构建道德规范理论时,他们基于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阈构建了各不相同的规范理论。沙夫茨伯里基于审美视阈理解情感的道德价值并构建道德规范理论,认为情感的道德价值不会来自某种单一类型的情感,主张从美或丑的情感秩序出发理解情感的道德价值,由一种或几种情感形成的情感秩序若能使人产生愉悦的美感,则是道德的情感,反之,则是不道德的情感。因此,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无异,在对情感秩序进行审美判断的过程中,以审美判断为本性的苦乐感(下文简称审美苦乐感)被沙夫茨伯里视为道德规范理论的情感基础。该学说具有鲜明的美学色彩,19世纪英国思想家詹姆士·马丁诺(James Martineau)曾将其称为“美学性的道德”。本文认为,在对情感秩序进行审美判断的过程中产生的审美苦乐感无法为道德规范奠定有效的情感基础,更确切地说,情感与规范在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中呈断裂状态。就此而言,与其说沙夫茨伯里在18世纪初首次成功地构建起了一种以审美苦乐感为基础的道德情感主义规范理论,不如说他为道德情感主义哲学开启了帷幕,在为后来者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的同时也给他们确立了有待回应的理论挑战。
一、审美苦乐感:连接情感与规范的桥梁
沙夫茨伯里之所以极力强调情感并以之为基础理解和构建道德规范,源于他对洛克道德哲学的批判,尤其是他对洛克道德哲学提出的以奖惩法则为基础构建道德规范理论的思想的批判。在批判天赋观念(innate ideas)的过程中,洛克认为上帝、美德等观念都不是天赋的,也就是说,这些观念并非与生俱来就印入了人心:“不过这些观念(如果职责其物是天赋的,则这些观念一定都是天赋的)完全不是天赋的,因此,且不论说在每一个人心中,就是在爱研究、爱思想的人心中,这些观念亦是不清楚、不明白的。这些观念中,上帝的观念虽然似乎应该是天赋的,可是归根究底,它亦不是。”在谈及情感与道德的法律之间的关系时,洛克指出,蕴含在情感(欲)中的行动原则完全不是天赋的,为了赋予情感以规范,需求助于道德的法律中唯一的天赋原则也即奖惩法则(或刑赏原则),“道德的法律所以要颁给我们乃是要以约束和限制这些泛滥的欲望,而欲达此目的,则这些法律又必须以刑赏来平压人们在干犯法律时实所预期的满足。因此,人心中果真印有法律其物,则一切人类都会有一种确定而不可免的知识,都会知道,干犯法律一定能引起确定而不可免的刑罚来”。洛克在晚年指出,奖惩法则可为普遍道德共识奠基,它是全能者为了执行其法律而设定的行动法则,“可以有充分的力量,使人在选择时,违反了现世所能呈现出的任何快乐或痛苦”。简言之,奖惩法则在洛克的道德哲学中担当着道德规范的角色。批判并反对洛克哲学中的奖惩法则,既构成了沙夫茨伯里批判洛克道德哲学的起点,也构成了沙夫茨伯里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规范理论的理论基点。《论特征》强烈批评奖惩法则,认为奖惩法则不可被视为普遍道德共识的基础,在谈到被奖惩法则规范的主体时,沙夫茨伯里说,“这种被塑造过的生物,谈不上正直、虔诚和圣洁,不比被束缚的老虎温顺和善,也不比处于皮鞭惩戒下的猴子敦厚顺从。不管是这类动物还是处于相同状态下的人,其行为都可能被诱导,不受意愿的支配与促使,仅只受敬畏的支配而被迫服从。故,这种服从具有奴性,他据此而做的所有事也都只有奴性”。受奖惩法则支配的行为是被诱导的结果,没有自主性,只有奴性,根本称不上美德。为了使道德行为彻底摆脱因受奖惩法则的支配而产生的奴性,为了使富有美德的行为在彰显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凸显内蕴于自身的人性之光,沙夫茨伯里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使主体的道德行为和美德具有内在的情感基础。因此,《论特征》首先着重论证了情感,尤其是自然情感(natural affection)在道德和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由此在英国道德哲学舞台上拉开了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的帷幕。
道德规范源于道德判断,道德情感主义以道德赞同为核心讨论道德判断。沙夫茨伯里从“道德感官”(moral sense)入手讨论道德赞同、道德判断和道德规范的情感基础,不过,“道德感官”在沙夫茨伯里学说中的道德价值并不来自道德本身,而来自以审美为本性的“美的感官”(sense of beauty)。“道德感官”的内在运行机制与用以做出审美判断的“美的感官”相同,和五官感官一样,二者都不会基于天赋观念为主体提供规范原则。当心灵欣赏并热爱外在于自身的自然秩序时,“美的感官”承担了对秩序展开审美判断的功能。与五官感官一样,“美的感官”并非与生俱来就印入了人的心灵,故而由“美的感官”产生的审美判断或趣味也与天赋观念无关:“若无先在的批评之劳苦,合法且公正的趣味则既不会被人获取、也不会被人制造、设想或生产出来。”“美的感官”不提供天赋观念,由它主导的审美判断并非与生俱来的,人只能在不断进行批评实践的过程中日趋成熟。沙夫茨伯里认为,由“道德感官”主导的道德判断能力被视为一种新的、发现美丑的能力:“在具备了一种以新的方式观察和赞美的能力时,它必然会发现行为、心灵和性情中的美丑,正如会发现形象、声音或色彩中的美丑一样。”“道德感官”以审美为本性,与“美的感官”不同的是,“美的感官”主要用于辨识自然事物中的秩序之美,而“道德感官”则主要用于辨识情感中的秩序之美,二者都具有以审美判断为内容的相同职责,一如“美的感官”依靠审美苦乐感辨识秩序之美丑,“道德感官”也依靠审美苦乐感辨识情感秩序中的美丑,在展开判断的过程中,二者都排除了天赋观念,故,“道德感官”可被视为情感和道德领域内的“美的感官”。
沙夫茨伯里认为,由“美的感官”提供的审美苦乐感是规范美丑的情感基础,同理,由“道德感官”提供的以审美为本性的苦乐感也可被视为道德规范的情感基础。把道德规范的情感基础理解为审美苦乐感是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的独创,审美苦乐感之所以能成为道德规范的情感之源,就沙夫茨伯里理解的美自身的特点以及美善关系而言,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美自身的特点来说,美具有“一见到就会立即被承认”且能推动主体产生爱美之心或求美的行为的特点。同理,以审美为本性的“道德感官”对情感中的秩序之美表达的道德赞同也具有该特征。因此,高尚之人是致力于欣赏并沉思道德或风尚(沙夫茨伯里把风尚理解为道德实践)之美的旁观者。道德之美产生于道德情感的秩序之美,欣赏道德之美亦即欣赏道德情感中的秩序之美,这是一种“单纯的凝视和崇敬”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以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为特征的审美状态。进一步说,由于“道德感官”以审美为本性,它赞同的始终只有能使人产生审美苦乐感的情感秩序,因此,大凡有损情感秩序之美的动机或行为,不管是因公共或整体善之故,还是因私人善之故,都不会得到“道德感官”的赞同。沙夫茨伯里据此宣称,“支配人的,不是所谓的原则,而是趣味”。更确切地说,当“道德感官”表达道德赞同时,其根据不是以公共善或私人善为标准的道德原则,而是与情感秩序相伴的审美趣味。
另一方面,就美善关系来说,美的情感秩序与善的后果之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联性,拥有美的情感秩序能给道德主体自然而然地带来善的后果。美自然而然产生的善的后果至少有三种。其一是美能给凝神沉思或欣赏美的人带来审美快乐:“大凡对我们所说的雅致或文雅有了印象且熟知事物的合宜与优雅的人,都会在审视并凝神观照这种美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和享受。”在沙夫茨伯里看来,这种审美快乐自身就是善的。其二是美可以给事物带来繁荣并使之沿着符合其本性的方向发展壮大。沙夫茨伯里指出,和谐、对称和秩序可以使万物获得真正的繁荣且符合其本性,同理,不和谐、不对称和无秩序则不符合万物的本性并会使其走向偏促(incommodiousness)和疾病。推而广之,“用以产生美的同样的外形和比例,如果用于行为并加以利用,也可产生益处”。其三是,当心灵自身具有秩序之美时,美可以给心灵本身带来善。当心灵的内在比例没有被扰乱时,用以形成道德行为的情感就会产生秩序之美,这种美会给心灵带来善的后果,使其变得越来越优良、健康和繁荣。由于注意到美的情感秩序能自然而然产生善的后果,沙夫茨伯里进一步主张,道德的目的是美的情感秩序而非利益,故,在对情感秩序进行审美判断的过程中产生的苦乐感可以为道德规范原则奠定情感基础。
“美的感官”的主要功能是审美判断,伴随着审美判断的情感感受是苦乐感,审美苦乐感与爱美或回避丑的动机或行为之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联性:在知觉并享受审美愉悦感的同时,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爱美的动机与行为,而当我们知觉到不美的东西并感受到审美意义上的不快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回避它的动机或行为。令人愉悦的美感能推动审美主体自然而然地产生爱美的动机或行为,令人不快的丑感则能推动审美主体自然而然地产生回避丑的对象的动机或行为,审美苦乐感与美学规范原则在“美的感官”内部能自然而然地统一起来。在沙夫茨伯里看来,对于以审美为本性和主旨的“道德感官”来说,伴随着道德判断而产生的审美苦乐感也能推动道德主体像审美主体产生爱美或回避丑的动机或行为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道德动机和行为,换句话说,以审美为本性的“道德感官”能像“美的感官”在审美苦乐感和爱美或回避丑的动机或行为之间建立自然而然的关联性那样,在审美苦乐感与道德动机或行为之间建立自然而然的关联性。不过,这只是沙夫茨伯里的幻想罢了,笔者认为审美苦乐感和道德规范在沙夫茨伯里哲学中实际上处于断裂状态,二者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桥梁的断裂:对沙夫茨伯里的驳斥
就美自身的特点来说,如上文所述,美虽然具有一见到即被承认且能自然而然推动主体产生爱美或回避丑的行为或动机,虽然审美苦乐感可以为爱美或回避丑的行为或动机确立美学规范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以同样的方式为主体确立道德规范原则。更确切地说,为主体提供道德规范的情感基础,不是审美苦乐感,而是其他情感。与沙夫茨伯里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们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最早注意到了审美苦乐感与道德规范之间可能存在的断裂,他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用孩童将坠于火的例子为道德规范提供了一个审美苦乐感之外的情感基础。曼德维尔指出,一见到婴孩将坠于火就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只是出于缓解此情此景产生的令人痛苦的感觉而做出了该行为,而推动该行为的情感动机,不是对孩童的同情,更不是由道德主体的情感秩序产生的审美苦乐感,而是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自爱:“挽救一个将坠于火的无辜婴孩并不是什么功德。该行为既不好也不坏,不管婴孩得到了什么好处,我们仅仅只是被迫做出了这种行为,因为看到婴孩坠于火但却不尽力阻止会使我们感到痛苦,自我保存强迫我们做出了这种行为。对于同情心泛滥且痴迷于满足这种激情的人来说,更值得吹嘘的是自己把微不足道的小物体当作了释放同情的对象。”曼德维尔的孩童将坠于火的例子向我们证明,伴随着情感秩序而生的审美苦乐感与道德规范原则之间并不具有强制的关联性。相反,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松散的、可被取代的关系。退一步说,即使伴随着情感秩序而生的审美苦乐感能在“道德感官”的作用下推动道德主体产生道德动机或行为,它作为道德规范原则的情感基础也依旧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以丑的情感秩序产生的审美不快为例,如果道德主体知觉到了这种审美不快但却漠视之,对于该主体由此遭遇的损失或承受的后果来说,除了无法欣赏并享受审美愉悦感外,顶多还包括由这种情感秩序产生的、以疾病和灾害为表现形式的不善的后果,除此之外,该主体并不会因此遭受更重、更难以承受的后果,比如良心的谴责等。
就美善关系来说,如上文所述,沙夫茨伯里认为美的情感秩序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善的后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受“道德感官”的主宰而生的审美苦乐感能与以善的后果为指归的道德规范原理直接具有不可被替代的理论相关性。尽管美的情感秩序和善的后果之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关联,但美的情感秩序本身并不是善之为善的原因,它顶多只是善之为善的表征或象征,就此而言,推动美的情感秩序得以产生的更深层原因才是连接审美苦乐感和道德规范的真正桥梁。对于沙夫茨伯里的后继者们来说,有待完成的重要理论任务就是要探寻美的情感秩序得以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据此为道德规范奠定情感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是对这一挑战做出的回应。
《道德情操论》认为美的情感秩序和道德善共有的情感基础是同情,以同情为基础而产生的合宜性是美和善共有的深层情感地基,更确切地说,尽管伴随着情感秩序而生的审美苦乐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善的后果,但这种情感自身并不被斯密视为善之为善的情感根源,他认为合宜性才是使情感秩序得以产生审美苦乐感以及善的后果的深层原因。斯密基于同情(sympathy)讨论赞同,这种同情既不同于休谟的同情,也不同于汉语中含有怜悯之意的同情,它指的是旁观者借助想象将自身置于当事人的处境之后产生的情感体验以及把自己的情感与当事人的原初情感进行比较的情感倾向。就此言之,所谓合宜是指旁观者和当事人在同情的作用下逐步调整自身的情感最终使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似的过程或结果。当事人和旁观者共有的处境为两种情感提供了可供比较的基础,合宜的情感意味着旁观者和当事人的情感具有以相似性为表征的对称美,反之,不合宜的情感则意味着旁观者和当事人的情感之间既无相似性也无对称美。为了阐明美之为美的根源以及善(或便利)之为善的根源,斯密进一步深化了沙夫茨伯里对美善关系的理解,他把基于同情而来的合宜性视为推动并产生美和善的深层原因,他指出,“适宜于使一切艺术品产生令人愉悦的设计通常会更受重视……产生快乐的手段通常比快乐本身更有重要”。美伴随着善与幸福,而丑则伴随着恶与不幸,我们之所以赞同美的情感秩序而不赞同丑的情感秩序,深层原因也是合宜性,用斯密的话说,就是“赞同的情感总是含有合宜的感觉”。总之,正是在合宜性这一深层原因的推动下,美或丑的情感秩序才使人产生审美苦乐感,也才能产生善的后果。
作为沙夫茨伯里哲学的后继者,通过深入分析美的情感秩序得以产生令人愉悦的审美感受和善的效果的深层原因,斯密深化了沙夫茨伯里对美善关系的理解。尽管美的情感秩序在《道德情操论》中依然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善的后果,但很显然,这种后果既不源于该情感秩序本身,也不源于由这种情感秩序产生的审美苦乐感。当斯密试图为美的情感秩序和善的后果寻求更深层的情感原因时,他的道德哲学已不再像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那样把审美苦乐感奠定为道德规范的情感基础,同情的合宜性取代审美苦乐感在这种道德哲学中为道德规范奠定了情感基础。更确切地说,斯密的道德哲学认为,美学规范原则和道德规范原则共有的情感基础是合宜性而不是审美苦乐感。
综上所述,不管是就沙夫茨伯里讨论的美自身的特点来说,还是就他讨论的美善关系来说,他最为重视的审美苦乐感并不足以为道德规范奠定情感基础。尽管用以表达道德赞同并做出道德判断的“道德感官”在沙夫茨伯里的哲学体系中被赋予了审美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足以为美学规范奠定情感基础的审美苦乐感能以同样的方式为道德规范奠定相同的情感基础。进一步说,道德赞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审美赞同,道德规范原则和美学规范原则从根本上说具有本质的差异。试图通过类比审美赞同的方式赋予道德赞同以审美本性并据此把审美苦乐感视为道德规范的情感基础,在道德哲学中是行不通的。如果说审美苦乐感借助“美的感官”能在审美情感和美学规范之间自然而然建立强制性的联系,那么,同样以审美为本性的“道德感官”则无法借助相同的审美苦乐感在道德情感和道德规范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相同的强制性联系。故,本文认为,情感与规范在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中呈断裂状态,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没有成功地为道德规范奠定恰当的情感基础。
结 语
呈现在审美苦乐感与道德规范之间的断裂状态表明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情感主义规范理论存有致命的理论缺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致力于基于审美苦乐感构建道德规范理论的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毫无意义,相反,不管是就其对17世纪道德哲学的革新来说,还是就其对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的创新性发展来说,审美苦乐感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就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对17世纪英国道德哲学的革新来说,当沙夫茨伯里发现审美知觉中含有无利害性并试图基于审美苦乐感构建道德规范理论时,这意味着他在人性中发现了一种以实现整体善为目的、以审美为内核的自然情感,从而找到了推动17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实现情感转向的立足点。就情感与整体善的关系来说,当情感使人产生以无利害性为特点的审美知觉时,该情感虽然不会直接以整体善为目的,但却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整体善,这意味着沙夫茨伯里可以在批评霍布斯提出的以自爱为主导的人性观的同时,为整体善的实现奠定一种新的情感基础和理论路径。对于17世纪英国道德哲学来说,沙夫茨伯里的这个新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革新价值。他把以整体善为指归、以秩序之美为特点的情感称为自然情感,在谈到自己的学说的主旨时,他明确说过,自己的哲学体系试图证明自然情感与国家、社会或同胞之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联结纽带:“对于以社会为自然目的的生物来说,服从自然的旨意为他自己的社会或整体善行动,实际上就是追求他自身自然形成的、名副其实的善,以相反的方式行动,或者说,受与那种共同善或公共利益相割裂的那种情感的支配而行动,实际上就是在追求他自身自然形成的、名副其实的恶。”进一步说,这种新发现不仅为沙夫茨伯里提供了反驳霍布斯道德哲学把自然状态理解为敌对状态以及与之相伴的、以不自然为典型特征的社会理论的新的理论基点,而且使之为一种新的自然状态学说以及与之相伴的、以自然而然为典型特征的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奠定了新的情感基础和理论地基。
就沙夫茨伯里哲学对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启蒙来说,当他明确指出具有审美苦乐感的自然秩序实际上源于自然的造化之功时,这意味着该派道德哲学终究会基于自然为道德规范奠基。不过,由于基于审美苦乐感探求道德规范的情感之源,沙夫茨伯里本人的道德哲学远未完成该派哲学最终将完成的理论任务。尽管如此,就“德性不与自然相反”来说,由于借助自然情感概念重塑了美德、自然以及人的自然能力之间的关系,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不仅在18世纪充当了复兴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先锋,而且还充当了新思想的启幕者。对于以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等为代表的后继者们来说,之所以在其著述中推行一种有别于霍布斯传统的、全新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其当代哲学渊源完全可以追溯至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
不过,尽管审美苦乐感不仅革新了17世纪英国道德哲学而且推动了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沿着新的理论路径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但它在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中实际上却始终未能为道德规范奠定有效的情感基础。事实上,正是在坚守沙夫茨伯里提出的基本哲学立场的同时不断超越或深化沙夫茨伯里对审美苦乐感与道德规范之关系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英国道德哲学才得以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提供了哲学基础与理论动力。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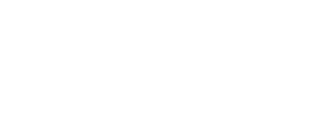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智库平台
智库平台


